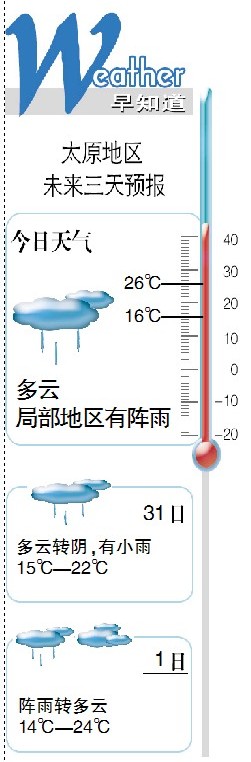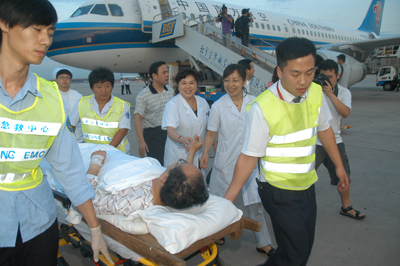裸模向《环球人物》杂志披露内幕
“人体私拍” 触目惊心
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说:“中国人体摄影界可谓是乱象丛生,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拍,什么人都能组织去拍,什么人都能当裸体模特,去参加人体摄影活动。我觉得这可以说是色情活动。”
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 黎影 鲍童
8月19日,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华茂大厦星巴克咖啡店的门口,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如约而至的南希(化名)。身材高挑的她穿着一身碎花垂地长裙,走起路来裙摆翩翩,引来周围许多人的目光。在一个靠窗的角落,南希坐了下来。记者半开玩笑地对她说:“大家都在看你呢!”南希的表情很淡定:“做我们这行的,已经习惯了在别人的眼光中生活。”她所说的“行当”,就是在所谓的“人体摄影”圈里当“裸体模特”。
两年前,在北京的一个画展上,记者认识了南希。那时,她还是一个扎着马尾辫、皮肤白净的女孩子,拿着自己的简历逢人便送。简历上写着:“××,21岁,就读于北京××学院,个人形象条件好,愿接拍影视剧、参演歌舞话剧、担当模特……”听到记者说起那时的她,南希笑了,转而又动容地说:“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,有时候,我自己都忘记了……”
“像我这样在模特公司上当受骗的女孩儿有很多”
“我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当模特或进入娱乐圈。能不能成为大明星不重要,关键是那样的生活太吸引我了。后来,我总算从老家(东北某地的一个小乡村)考到了北京××学院(一所民办高校)。那时候我觉得,只要到了北京,离当初的梦想就不远了。”可来到北京后,南希才知道现实离梦想依旧很遥远。她的同学大都是北京当地的孩子。“都很有钱,就没见她们为钱发过愁。而我不同。”记者很诧异:“我一直以为你家境很好。”南希脸上露出无奈的笑,“很多同学看我穿着时尚,业余活动也丰富多彩,还以为我的家境很好。其实,我爸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,姐姐很早就嫁人了。农闲时,我妈就在家里扎假花,一天下来最多能做200枝。她累得眼花、腰痛,但做一枝假花也只能赚两毛钱”。记者有些不敢相信。眼前的南希画着浓浓的眼妆,从配饰到裙装,都搭配得非常得体,就连指甲都用亮片精心修饰过。“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,我从来不向别人提家里的事情,如果有人问我,我会说老妈是做生意的。其实,我很讨厌自己这样,生活是假的,自己也是假的。”记者问她父亲的情况,她摆摆手:“不提他了!”然后又说:“这里可能不让抽烟,我们到外面的位子坐吧。”
南希到北京后,一直没把精力放在学业上,只想着进娱乐圈。她也曾当过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。有一次,她偷偷记下了张贴在学校门口的模特公司的招聘电话。“他们的工作室在三元桥(位于朝阳区)附近的一个住宅区里,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。”对方声称,一位知名导演在为电视剧物色一个小角色。“那天去了很多女孩儿。我们先填写一个表格,然后挨个儿拍照。对方说,要拿给大老板看。”几天后,那家模特公司又把南希叫来,说她的条件和气质都很符合要求,希望可以合作,但要她先交1000元的“试装费”。“我压力很大。我妈要扎多少枝假花才能赚1000块钱啊!”见南希犹豫不定,模特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劝她说:“赶快交了吧,说不定这个角色能火,到时候别说是1000块,就是1000万也能赚回来。”南希思来想去,最后狠狠心向母亲预支了两个月的伙食费,还向好友借了300元钱。
“交完钱,等了一周也没消息。后来我打电话问,他们好像都把这事忘了。我报了名字,并说自己已经交了钱等着拍戏。他们马上又说:‘你快来试镜吧,都等你好几天了。’我当时就想,不是角色都确定了吗?怎么还试镜?”南希于是又一次来到那家模特公司。可对方说那部电视剧换导演了,得重新交“试装费”。“我当时心就凉了,知道自己上当了。”
南希回忆着那段经历,顺手点了一支烟。“那阵子,我每天只吃一顿饭,真的是一顿。有一回,一位老家的熟人来北京,我琢磨着总要请人家吃顿饭。人家见了我,半开玩笑地问:‘你是不是吸过大麻啊?怎么眼角周围都是黑的?’他不知道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。那顿饭最后还是老乡请的。”南希弹了一下烟灰,接着说:“我印象很深,当时要了一份干锅鸡,其实鸡肉已经吃完了,只剩下一点茶树菇。但我对服务员说:‘这个菜也打包!’”
南希说:“像我这样在模特公司上当受骗的女孩儿有很多。我们没有钱,也没有背景,特别容易被别人利用。即使没有坏人,自己也可能不知不觉就走到出卖脸蛋甚至是身体这一步。”
“一些人冲什么而来,我们都心知肚明”
一个多月后,那家模特公司一个给南希拍过照的摄影师找到了她,问她愿不愿尝试一些其他的赚钱门路。“他把我约到他家里,然后给我讲人体拍摄是一门艺术,很高雅也很专业。‘这门艺术现在已经慢慢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,既安全稳定,又不会太辛苦,最关键的是赚钱多、成名快。’”
赚钱多!成名快!南希于是下定决心去做一个“人体模特”。此时,她还弄不清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职业。摄影师告诉她,他将人体摄影视为艺术生命,曾经一连试了10多个模特都觉得不满意。“当时,我觉得他是一位高尚的艺术家。”说到这里,南希猛吸了一口烟。“他问我能不能把身体展示给他看一下。我简单地做了几个动作后,他就让我把外衣脱掉。我羞涩地站在那里。他又鼓励我说,一定会帮我成名。于是我答应了他。”
就这样,南希开始了“模特”生涯。“那次就是在他家一间大卧室改成的工作室里拍摄的。里面放着一些专业的摄影灯、背景幕帘、反光板等器材。”南希看着这些专业设备,紧张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些。“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份工作。呵呵,现在看来,不过是在自我安慰罢了。”第一次赤身裸体地站在一个男人面前,南希说她当时“很害羞”,磨蹭了半天才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掉。“脑子一片空白。之前想好的动作全忘了,浑身肌肉紧绷,一直低着头,连毛孔都是紧张的。当他用相机镜头对着我私密处时,我本能地用手挡住或者转过身子。所以,他拍的几张照片都很模糊。这时,他拿了3000块钱放在我面前,跟我说:‘本来都是要给你的,可是看你怎么也没有状态,拿500块,你走吧。’我当时就急了,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状态。那家伙对我说:‘必须有专业精神。你要是愿意,我可以帮你克服这种紧张心理。’”回忆到这里,南希又点了一支烟,手抖动得很厉害。“他帮助我的办法,就是扑上来抱住我……”那次裸拍,南希拿到了3000块。那是她生平赚到的第一笔“大额报酬”。可她并不快乐,“比死还难受”。
南希告诉记者,她平时接的活儿主要有两种:私拍和群拍。“私拍”,参加者限定为1至3人;“群拍”则一般被限定为4至8人,有时也能达到20人左右。不管是哪种方式,都存在各种风险。记者问南希是否被骚扰过。她抿了抿嘴,只说一个同伴有过。“有一次是群拍,其中一个‘摄影师’以‘调整模特姿势’为由,上来乱摸。女孩儿狠狠地把那个脏手甩开,那家伙就用烟头烫她的手腕。还有一次,雇她的一个‘摄影师’对她动手动脚。那个女孩子最后哭着回老家了。”说到这里,南希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的表情。“等把钱攒够了,我就去美容院或者公司找个正经的工作。”
既然如此看低这份“工作”,南希为何还要坚持呢?她当然是为了钱。在很多人看来,南希挣的那点钱不算什么。但她觉得报酬还算不错,所以才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儿愿意去做。“人体模特之间彼此很少接触。但是我知道,从事这个行业的,除了像我这样的非专业‘模特’、跑龙套的女演员,还有不少是‘小姐’,甚至还有清洁工和卖水果的。”
南希告诉记者,群拍时她的心理压力最大。“当一个女孩子在众人面前脱光衣服时,感觉就像面对万丈悬崖。当然,有过那么一次经历之后,你就会放松很多。最高兴的是遇到专业的艺术摄影师,他们是冲着艺术和美而来的。但是,其他一些人冲什么而来,我们都心知肚明。但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”
其实,“南希们”最担心的是照片被外传。从第一次接受裸体拍照的那天起,她们就终日生活在紧张和恐惧中,怕这些不光彩的事被公布,从而遭到家人的唾弃。小莫刚入行不久,曾多次跟南希说起这个问题。“过来人”南希总是安慰她:“既然担忧没用,不如放松些!”